
川久保玲是時尚界無人不知的名字,圍繞她身邊的人,都無可避免地沾上光環,受到媒體吹捧愛戴,唯一例外的,也許只有一個人,他背著 「川久保玲御用插畫師」之名,與川久保玲惺惺相惜合作無間,卻隨和低調得不為人所知,他是 Filip Pagowski。
有些設計師,成名後便迫不及待顯露自己的意氣風發,也有不少得到名與利卻也不被沖昏頭腦。Filip Pagowski靠著川久保玲這個響噹噹的名字,好像除了為他帶來一點點名氣以外,幾乎 沒有改變他對創作的態度。Filip不擅推銷自己,也不貪心,因為在整個時尚或設計版圖裡,他根本不算什麼,他默默地專注於自己的平面設計工作,仍堅持用手繪草稿繪畫,以一貫充滿人性個人化的畫風表達思想,絕不像許多設計師輕易成名不久,就把自己慢慢建立的風格壞掉。

出生於波蘭華沙的他,父親與母親均是當時著名的藝術家與畫家,小時候就在濃厚的藝術薰陶下成長。他反叛,在波蘭擁有藝術世家的背景,在23歲時卻決定到紐約大蘋果闖蕩天下;生活在美國卻也討厭美式漫畫、流行文化、從訪問的對答,看得出Filip是個有趣且直接的人,他不論性格與作品,都讓人感覺年輕活力,甚至不能叫人相信,他已是一個18歲女孩的父親。(當時《PPAPER》採訪他是在2007年)
有人終其一生仍自覺懷才不遇,也有人彷彿命中註定遇到伯樂賞識。Filip與Comme des Garçons的相遇,是偶然也彷彿冥冥中有主宰。真正展開合作之前,他已為Comme des Garçons客串當模特兒(川久保玲曾經用過一系列非專業模特兒包括不知名酒保、演員Dennis Hopper及歌手Lyle Lovett等人),模特兒太太也曾為Comme des Garçons走秀,至1999 年,他才正式開始他的Comme des Garçons歷險,由第一本服裝目錄、2000年的男女服裝以至2002年的「PLAY」系列。「川久保玲讓我感覺到,我是個全方位的平面『設計家』」,Filip的才華是完全地被發揮,這都來自川久保玲對Filip的信任。做時裝向來要求極高,川久保玲卻表明不是要Filip去配合她的衣服,而是將Filip畫作的獨特性發揮。連Filip也自言,他總是驚訝於他的設計在衣服上所衍生的創意應用。我們眼中的川久保玲,是前衛不規則,數十年來一直影響著時裝的潮流。Filip眼中的川久保玲,則是直接、簡單、富有邏輯性哲學,叫他興奮也能激發靈感的客戶與創作家。

與時尚界的合作多年,Filip卻自言不是個很fashionable的人。「Fashion是一種散發自內心的優雅,與那個設計師那件名衣無關。一昧追求fashion的人其實很可悲。」他眼中的fashion,應是種獨特與原創,從來不是自己是否跟得上潮流。這個亦同樣應用於視覺藝術或流行文化,潮流並無意義,好的作品來自設計師的風格與獨特性,用根本的創意去對抗膚淺的流行。Filip在Comme des Garçons上得到發揮空間與名氣,但其實不管是大牌小牌,他所投入的精力也是百分百的。在雜誌《The New Yorker》、《visionaire》、百貨公司 Barneys New York以至另一位時裝設計師Diane von Furstenberg也能同樣看到Filip的色彩斑斕、玩味還有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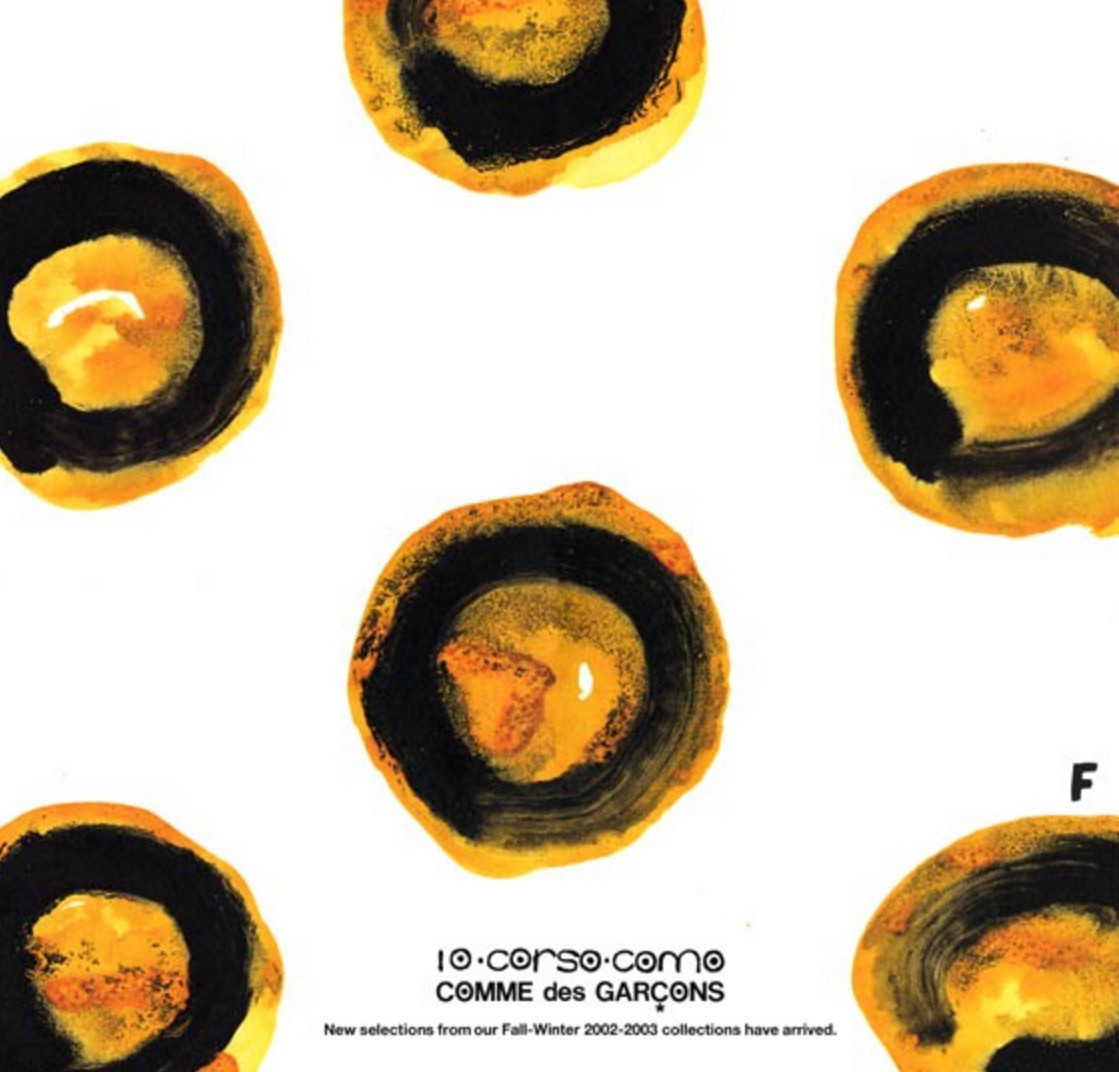
10 corso como x COMME des GARÇONS
創意成熟需要時間,Filip累積了廿多年的創作經驗,結出與眾不同的成熟果實,但這不是源於他被川久保玲慧眼選用,而是因為與很多平面藝術家相比,Filip的背景特別:波蘭60-70年代的成長環境,給他非常傳統的訓練,當時波蘭的藝術創作環境並沒有很富裕,在有限制的環境下,他練得更獨立更自力更生地尋找資源,他會由零開始,將想像繪成草圖,儘量不去用現成的影像或攝影去融合而更去想創意的方法去表達。一直以來,Filip的畫作所使用的技術都很簡單,他不是要刻意與科技或電腦抗衡,他只認為電腦永遠是配角,思考才是最重要,他享受手繪草圖的不完美與驚喜。Filip會形容自己的作品原創且很home- made,在這個不太喜歡用心費力的年代,他的home-made創作,承載了一份難能可貴的堅持與執著。
思考、反抗,努力樂在其中,創新也擁抱傳統,是Filip Pagowski對年輕一輩的勉勵。

訪談
PPAPER
╳
FILIP PAGOWSKI
你可以簡單介紹你的背景嗎?
我父母都是藝術家,媽媽是畫家、爸爸是已故的平面設計師Henryk tomaszewski,而我是他們唯一的小孩。小時候,我經常看我爸媽工作,當媽媽畫畫時,我不能去打擾她,但只要我不問太多問題,我就可以陪著我爸。記憶所及我從小就開始畫畫,而且我對繪畫充滿熱情,繪畫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同伴,也是我的所有。
我父母鼓勵我畫畫,有時會得到他們的指正,但也會因為好的成品而得到一些獎勵。在學校,我常因為上課偷畫畫惹上麻煩,但我也因為畫出來的作品得到同學間的尊敬,他們甚至還會拿東西來跟我交換,我們也沒有漫畫書,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個同學不知道從哪兒取得北歐的漫畫書,當時每個人都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辦法交換這些作滿記號的漫畫,但沒有人看得懂奇怪的北歐文字,所以大家只能非常純粹地欣賞,分析那些線條還有畫面。這也讓我之後,想挑戰重新畫出來,另外我們電視上鮮少卡通,儘管星期天早上有播,但大家通常都還在睡覺。我覺得我們很幸運地小時候沒有受到漫畫、卡通的污染,美國人都已經被這種文化洗腦,而使大多數的人停止他們的視覺接收新的東西,這就像吃習慣垃圾食物不允許味蕾培養敏銳度去品嚐真正的美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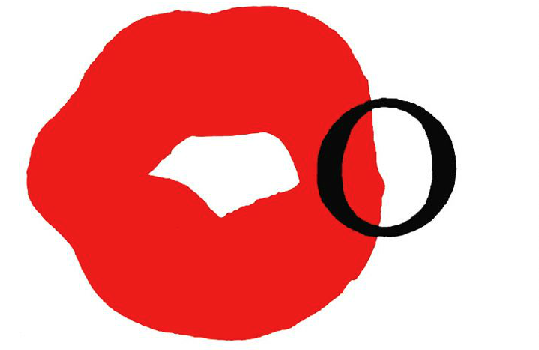
你怎麼開始你的插畫藝術家生涯?
我很早就知道我命中註定做個藝術家,我覺得當一個畫家很酷,但我更喜歡商業平面藝術,因為那必須用聰明巧妙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讓事情變好。所以儘管我在華沙藝術學院裡完成我大部份的學業,積極地在我父親的班上學習畫海報,在其他老師的課學插畫。但我在畢業前就離開波蘭,前往紐約,然後就開始為報紙與書的封面畫插畫。我的工作不多,因為許多藝術總監抱怨我的個人風格太強烈,他們總是說「你的影像非常強烈」但我天真地以為那是種恭維,直到一位在Doubleday出版社工作的年長藝術總監跟我解釋,他認為他可以看到我的天分,如果我能重新準備我的作品集,他會考慮給我一份工作。結果我很懶得做這件事,所以一切就成為歷史⋯⋯。

你的設計哲學是什麼?
我對設計的想法,從我還在華沙唸書的時候就開始醞釀。1960年代在波蘭有一群相當重要的平面藝術家,這些人的創作也就是外界所稱的波蘭海報學派,由於我父親比大部分的藝術家年長一些,自然成為那波新海報運動的指標性人物。那是一段被世界推崇,鮮明而且容易辨視的30幾年,但當新的政治情勢來臨,惡劣的經濟環境導致收入越來越少,年長的設計師退休,年輕的創作者迷惑於西方視覺的創意,也就是流行文化,逐漸取代了當地的視覺語彙,而使這波運動終於在八〇年代結束,這些藝術家包括:Jan Lenica(以 卡 通 電 影 聞名)、Roman Cieslewicz、Jan Mlodozeniec、Waldemar Swierzy、Franciszek Sarowieyski、Wojciech Fangor(同時也是位成功的畫家)、Jerzy Jaworowski等。他們的一致性在於他們作品中以複雜熟練的想法,融合簡單的技法,創造出富裕,有趣和有力的影像。
他們受限於貧窮、戰爭破壞、政治所造成的不快樂,同時在技術支援上的經費相當短缺,攝影太貴而活字排版方式基本上也不存在了。因此,有大量的影像都是源於結合手工印刷的繪畫(通常都相當地有個性而且主題明確)。一個好的設計師必須是一個天才手藝者,懂得欣賞字體學(typography)而且有能力預見他的作品在低品質的印刷水準下,能夠保持圖像的有趣和可溝通性。
這一切環境都迫使設計師,如果想要成功,就得培養相當明確的設計語言,也因此儘管每個設計師都有非常顯著的個人風格。但他們對於設計的態度卻讓他們團結,相較於現在超過99%連畫畫都不懂的平面設計師(日本除外),他們的與眾不同,反而帶來另一道不可小覷的特殊風格。
現在,回到我身上。我離開波蘭的時間越久,我越覺得這些傳統帶給我的影響,是這個電腦時代裡冷漠與機械化的解毒劑,用我的文化根源,結合我看全球化下的現代影像文化,所發展出的創意,就成為我的哲學。

你出生在波蘭現在住在紐約,哪邊是你生活或居住最喜歡的地方?
我從未真正在波蘭工作過,當我開始住在紐約後,我在一些波蘭的出版社做過事,這非常有趣,但從這樣的角度我不敢說我了解波蘭的插畫或設計市場,看見我的一些朋友們在做插畫或設計,我覺得他們的工作相當多采多姿而且有趣,即使這和我還是個小孩所看到,或在華沙藝術學院唸書時有些不同。
你認為你哪件作品最能代表你?
我不認為有哪一件單獨的作品能夠代表我的專業,原因是我仍然希望,未來仍有作品能夠讓我和其他人更驚喜,也想探索比我現在認為更多、更好、更不同的我,我覺得我還在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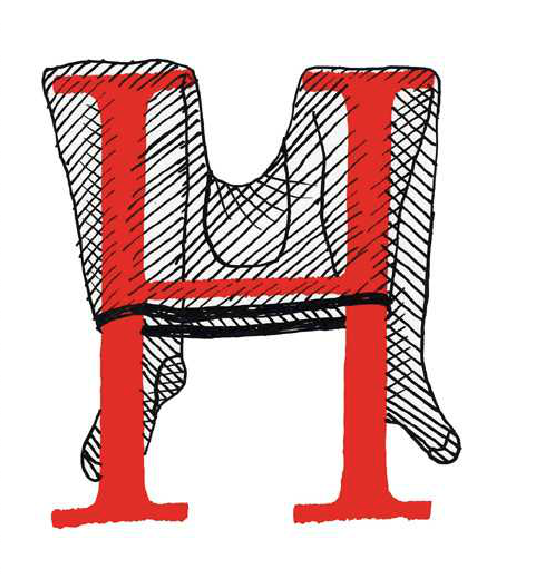
在每一個案子裡,最引起你興趣的是哪部分?
說到這,我必須承認我與Comme des Garçons合作的過程,使盡了我所有才華,而且讓我感覺我是個全方位的平面「設計家」,這大部分要歸功於直接、簡單而且邏輯性哲學的川久保玲聘請我時,她給我相當多的信任,我知道Comme des Garçons作品的品質,也期許他們會有相當多地要求,我卻非常快地了解他們就是想要我所代表的獨特性,這表示他們百分之百的相信我,而且想要我的建議和解決方法,而不是只是要我去執行他們的想法。我想,這讓我做得更好,想得更深,而且更樂在其中。
客戶經常沒有完全看到,我為他們做的這些作品裡的潛力,他們對於某些出乎意料的驚喜感到困擾,但與Comme des Garçons的合作,我總是驚訝於他們使用我的設計所衍生的創意應用。



COMME des GARÇONS
你目前所遇到最具挑戰性的案子是什麼?為什麼呢?
每一個我在做的案子,對我來說都不同。因此,情緒、感覺和態度上全面地轉變,可能會從悲慘到非常快樂,有時我會以戲謔地心情檢視前一件作品。當然,我們通常從一開始就明白事情會不會成功,如果真的成功的話,那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
具挑戰性的案子也是同理可證。案子有大有小,有簡單有複雜,也許,有時只是單純地害怕,但我相信工作會接二連三地來。因此,所有的工作都應該認真對待免得這個連續性斷掉,規模通常意味著重要性,因此我對案子的整體概念感到興趣,大的案子或更複雜的案子,意味著需要更多計畫,策略和協調,但就像是大戰役與小戰役,仍有人會在小戰役中喪生,所以提高注意力是必要的。
挑戰也會來自客戶,任務的屬性,一個企劃所要傳達的訊息,或環境和大眾會得到的衝擊⋯⋯等等。有些真的很困難,有些只是在於誰能為視覺想法找到正確地平面設計語言來溝通。


COMME des GARÇONS SHIRT
在你事業與生活上目前所碰到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最大的危機是身為一個自由工作者,得為自己奮戰。決定來紐約使我成為「平民」,但當時我不知道,那時候太年輕,好奇而且天真,這也意味著勇敢跟愚笨,或都有。
對你來說顏色是什麼?
顏色非常重要,通常具有決定性的效果,但我鮮少關注他們之間的細微差異,顏色就像是聲音,而我希望有個好鈴聲,讓我試著用畢卡索的觀點來描述,他認為當他無法使用藍色,他就試著用紅色,就會產生一種效果,當然那是一種誇大的說法,卻代表了多重意義。顏色是一種抽象的工具,就像是音樂裡的聲音,一種與現實較少連結或可以參考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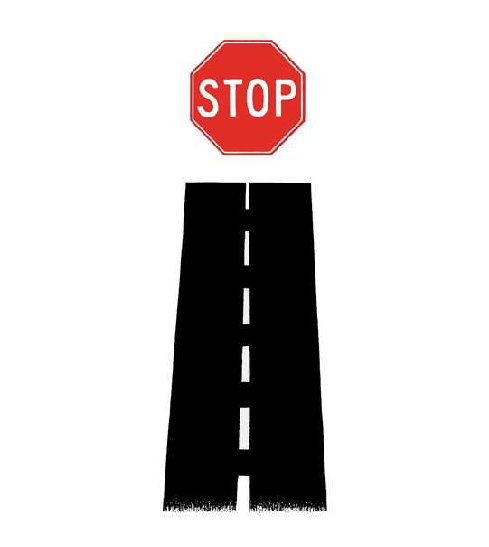
你認為Fashion是什麼?
Fashion,哇那是個大問題。這樣說好了,風格在所有事物當中都相當重要,食、衣、住、行、說、寫、設計、思考⋯⋯任何事。風格就像是種優雅,如果你能表現得宜或表現自己,而使自己成為某種⋯⋯風格,對我來說那就是fashion。當然,fashion也有另一個面——趨勢奴隸般的人,執拗地選擇做個追隨者,而不願成為獨立思考的人,那非常無聊,而且一昧追求fashion的人認為平凡人很可悲,但其實他們跟自己最想劃分界限的人一樣可悲,我認為fashion是種獨特與原創,而不是反應自己是否跟得上潮流(同理也可說明在所有的視覺藝術或流行文化)。我沒像一般人認為得對fashion那麼有興趣,這樣比較健康,而且不用太努力就可以遠離不當的媒體。

那並不代表我不喜歡美麗,設計良好的衣服,或者說我不讚賞那些剪裁技法。我7歲到11歲那個年紀時,在我父親的工作室中,發現一本有關各年代的戲劇服裝書,並且為它深深著迷,我結合了這些不同的樣式(從以前到現代)融入每天畫得騎士、希臘和羅馬的士兵、海盜、牛仔和印地安人,還學習基本的裁縫技巧。我還為我的泰迪熊縫製了一套海盜服,我甚至想過長大後,我會成為一個裁縫師,當時還不知道有時裝設計師這樣的行業。這些讓我知道,對fashion來說,都只是不同的年代、不同風格、和不同樣式而已。總括來說,fashion 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優雅。Comme des Garçons和一些日本設計師、Adeline André、Vivienne Westwood等,都是我喜歡並且尊敬的。



對你而言,電影是什麼樣的東西?
從前電影、導演和製作電影的技術對我相當重要。我說從前,是因為現在的電影對我來說不再那麼具有份量,這是我的印象,我並不期待一個認真去從電影中尋找快樂的20歲年輕人同意我的想法,但最近我比較少看見像是1978年以前的電影裡,具有張力、有清晰的意念、整體也很一致,有些事情改變,像是大量的外星人、星際大戰等類型的電影,讓藝術形式減低了。當然還是有些例外,有時我也懷疑是不是字彙愈加貧乏了,也許是時候該有新的形式或新媒體的出現,帶給我們像是100年前電影給大眾的衝擊。八〇年代中期,我那時製作音樂錄影帶,並且嚐到整個過程和工業的新滋味。1987年,我製作了一部12分鐘,只有兩位演員的電影,並且加入由Arto Lindsay和Nana Vasconcelos製作的有趣音樂,之後我開始製作卡通,並且非常樂在其中,我非常希望能多做一點。當然,電影製作中有太多最好的方法去呈現一些事物,如何去營造一些感覺、氣氛、情緒等等,這些都非常令人興奮和瘋狂。
你怎麼描述或定義你自己?
我怎麼能描述或定義我自己?

你和其他平面設計師有什麼不同?
和其他平面設計師比起來,我來自一個不同文化的世界,生長在六〇到七〇年代的波蘭,被風格明確的平面藝術和藝術環境所包圍,我的雙親也是藝術家,這些都對我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學習去掌握有限的優勢,甚至去享受它們。我盡可能的利用素描將影像做到最好,而不是利用既有的影像去做(譬如說攝影)。那是必須的,因為波蘭的平面設計或印刷工業相當的匱乏,相較於那時候的西方世界或日本來說,在技術水準上相當侷限,但這樣的情形,迫使設計師或平面藝術家們,能夠發展出一種不同、獨立,而且具有更多創意和到現在都適切的視覺。(舉例來說:Comme des Garçons在2006年秋天的男裝秀裡,使用了四張我父親,Henryk tomaszewski,六〇、七〇和八〇年代不同的海報,在襯衫、夾克上表現不同的創意。)也許我從來沒有學習到攝影的魅力和張力,如何去應用在平面設計上。因此,我對充滿「home- made」的作品感到舒服是很自然的。另一個對我的影響,反而是自由,沒有任何商業壓力,沒有廣告,也不用替客戶擔心賺錢或賠錢。我認為這些可以定義百分之五十的我,而另外百分之五十則是我離開祖國後,在紐約的一切努力。所以,我真是矛盾⋯⋯。

你接受客戶委託時,你的顧慮是什麼?你怎麼決定接受與否?
我很少在接受客戶委託時,考慮怎麼去做。工作就是工作,而我必須去做。有時候你可能會對有些工作失望,也或許有些案子和我相當契合,但每一個案子都是我們應該接受的挑戰。當然,有些案子和我的政治或商業立場明顯不同時,我可能會拒絕。但我喜歡多樣化的工作,以及許多不一樣的客戶。我在其中找到樂趣,而且讓我的領域變得更廣。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些你和川久保玲工作的經驗嗎?
和川久保玲一起工作永遠都是個經驗。我已經在早先說過,和Comme des Garçons一起工作是多麼地有趣。
不幸地,有極少的客戶能夠像她一樣那麼有自覺,閱歷資深,在視覺上相當大膽,願意讓原本的需求來適應一個新穎的視覺。也因此,除了開始明確,這些工作完全開放,沒有方向,甚至沒有特定方式可以解釋。有了大量的自由,卻創造了一個挑戰,如何對準目標去實踐,因為大部分人其實都不知為何而創作,我偏向依靠感覺,而我都會做於要求的作品,去掩飾我的不足同時提供更多不同的解決方法。川久保玲通常都會將我這些額外發展出來的提案,用在Comme des Garçons其他的案子上,當然,Comme des Garçons是一個會讓我興奮也能激發我靈感的客戶,當川久保玲選擇要我在1999年秋天與她合作,這代表她認同我的作品值得與她的設計相提並論,讓我非常榮幸。



COMME des GARÇONS
其實我與Comme des Garçons之間有段非常有趣的故事⋯⋯我第一次替Comme des Garçons工作是在1999年11月底左右,那是一本女裝的brochure(包含9個畫面、黑色蒼蠅、貓、朝鮮薊、山⋯⋯等等)。將會在2000年擺放至店面,他們不讓我看女裝,希望我的作品不是依據他們的作品,而是要很「我」的圖像,由於我製作了很多,所以他們從中挑選了9張,同時使用在其他地方,兩張用在Comme des Garçons的襯衫廣告,還有一兩張用在節令賀卡。接著,身為Comme des Garçons的商業總監和川久保玲的老公Andrian Joffe問我,是否有興趣為2000年男女秋裝設計圖像,靈感來自龐克運動,但需要將視覺「更新」為2000年的版本,接著2000年3月又做了一本brochure——白色小鳥襯著灰色背景,還有些我已經不太記得的元素,從那時候起我就一直斷斷續續地和他們合作。「PLAY」這個系列的構想在2002年生出,那時還有其他,像是「robe de chambre」在日本的圍巾系列;Comme des Garçons在米蘭和Corso Como與在巴黎和Collette,還有無數的賀卡和通告。我最新的作品是「PLAY」紅色心型系列的「表弟」, 一個綠色的心型lo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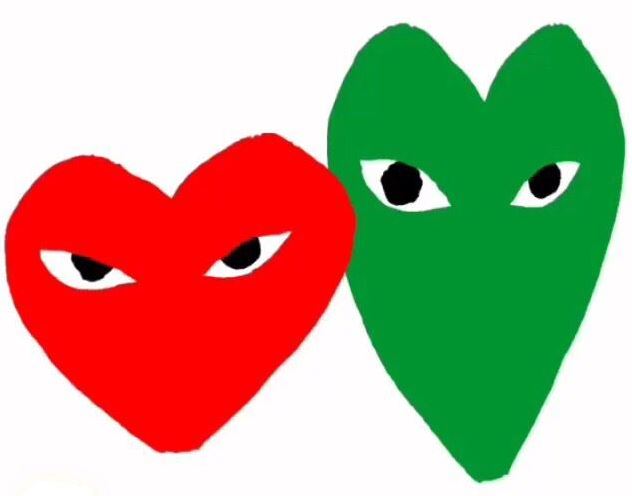
COMME des GARÇONS PLAY
我計畫也希望和 Comme des Garçons有更多的合作機會。2006年10月我才和Adrian在巴黎就討論了一些可行的計畫⋯⋯但我跟Comme des Garçons有一段長久而隨性的關係。從80年代早期,我當時的老婆Dovanna是個時裝模特兒,開始在巴黎替Comme des Garçons走秀,當時我們也和我們的雕刻家朋友Daniel Wnuk,一起創作了結合表演藝術的時裝秀,由Dovanna穿著水泥製成的洋裝組成,並且在紐約的Danceteria演出。之後我們將表演的照片寄給川久保玲,她回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們,然後透過Dovanna,我認識了在美國負責Comme des Garçons的人,在某些場合上,他還讓我在紐約當Comme des Garçons的模特兒。之後1992年我去東京旅遊,我碰到了Comme des Garçons的人,他們非常大方地帶我母親和我體驗東京(邀請我們去看Comme des Garçons還有山本耀司的秀)。同一年夏天,我又被請去參與Comme des Garçons在巴黎的男裝秀中當模特兒,而我只是一群非模特兒中的其中一人,其他人還包括Lyle Lovett, John Hurt, Osie Clark, Brice Marden, Jon Hasell⋯⋯等等,都是些非常有趣,非常成功的藝術家、演員、設計師、音樂家⋯⋯接著,就是1999年的合作案了。好笑的是,川久保玲完全沒察覺到我之前替Comme des Garçons做了什麼,她想用我是因為她「發現」了我的作品,而不是透過一些人際關係。


《DUTCH》雜誌在2000年11、12月號(30期)做了Comme desGarçons和川久保玲的專訪,而川久保玲曾在訪問如此形容我:「我想在2000年的秋冬呈現強大的活力。這是我對最近看到了無新意的無聊衣服所作的憤怒反應,我最初的想法是表現搖滾龐克文化內固有的能量,而能使它符號化的是Pagowski,一個在紐約的藝術家,他極出色的圖案和筆觸,在此季裡將這種精神捕捉得活靈活現。」也因此之後執行編輯Rebecca Voight打電話給我,確認是否有我這個人存在,因為她從未聽過川久保玲如此讚賞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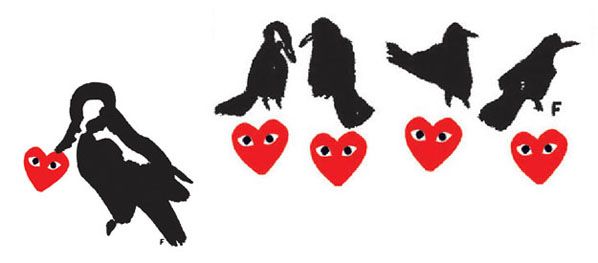
COMME des GARÇONS PLAY
和Diane von Furstenberg一起工作是怎樣的經驗?
和Diane von Furstenberg合作其實是個意外。她在06年的春裝,還有bergdorf Goodman百貨主辦一場紐約新當代美術館的義賣活動中所設計的洋裝與汗衫上有使用我的一幅畫,結果06年的夏天,Diane von Furstenberg委託我為07年「關於夏娃All about Eve」春裝發表秀中主要的洋裝設計圖案。那是個非常具體的圖案,一條蛇圍繞著洋裝本身及穿著洋裝的人體,而我試著讓蛇的圖案連續,不會因為任何的接縫而間斷,但從我接下這個案子的當天就慢慢演變,結果必須讓圖案與春裝的其他系列相稱協調,我到今天都還不知道到時候在店裡面的結果會怎麼呈現(訪問當時是還未發表),這不是我能夠決定的。這兩個設計師完全不同,一個是代表美國時尚主流,另一個則在這三十多年間掀起時尚界的革命。她們兩位我都非常敬重,也希望能夠有再和她們合作的機會,儘管和她們兩人合作的經驗,兩人作品的風格都大不相同,但我都非常欣賞而且總能夠從中學習。

你的創作概念都來自何方?
概念來自我的腦袋。有時,那就像火花,有點像「阿!想到了」的經驗。有時候會從插畫、素描,或其他的方式出現,有時你也可能看到毫無相關的東西,卻能引導你發現答案。
技術有提高或改變你的工作方式嗎?
我使用的技術非常有限,假如我使用電腦,主要用來找到最好的協調性,或修圖。我在家會多使用電腦來盡可能發展我的風格,但那對我來說還只是個實驗性階段,我對於卡通連續畫面大部份還是靠思考,雖然我知道電腦可以給我更多的選擇。通常,我喜歡在不受電腦控制的環境中,發生的不完美和意外。我到現在還使用有某些色彩選擇的老舊類比黑白影印機,印起來像舊式的平版印刷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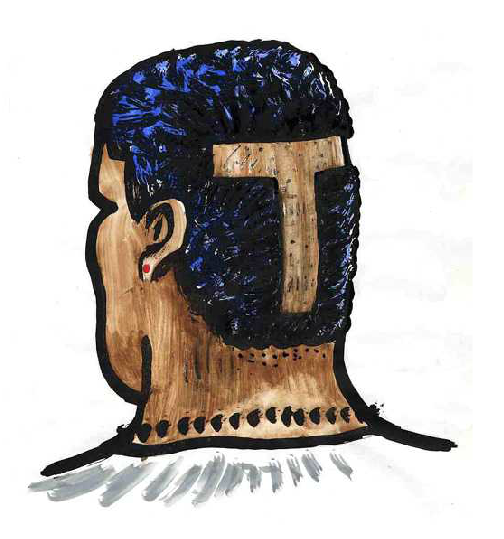
你最喜歡的藝術家或設計師是哪位?為什麼?
我不知道誰是我最喜歡的藝術家,有太多好的藝術家可以選擇。我的品味兼容並蓄,而且我也很喜歡這樣,許多形式的藝術都能激發我,像是平面設計、插畫、繪畫、雕塑或建築,我喜歡電影,也喜歡戲劇(當我住在波蘭的時候)。越多視覺元素越讓人愉快,有太多概念或裝置的藝術,通常讓我感到無趣,像是那些帶有有限視覺影響,由文本、說明或理論主導的文學作品。
這些是我所列舉,對我視覺呈現有相當重要影響的人:Pieter Bruegel the Elder、Saul Steinberg、Antonio Tapies、K2 Design Group(日本)、Witkacy(波蘭藝術家,1939年過世)、Alberto Burri、Ana Mendieta、Pawel Susid(當代波蘭畫家)、Norman McLaren、Caspar David Friedrich、Gordon Matta-Clark⋯⋯
為什麼呢?因為它們非常特別,深刻地、明確地、真實地、充滿張力和獨特,這不表示我就會抄襲他們作品,但他們的確啟發著我。

誰對你的影響最深?
這是上個問題的延伸 。我不知道,那比較像是一種感覺或是對我藝術上明確方法的影響。我的雙親,包括我的父親,Henryk tomaszewski,他是個海報畫家、插畫家、佈景設計師,也是教育我的人,同時我的母親,TeresaPagowska(在波蘭的拼音中有個a),也是個畫家,我在他們陪伴中成長,觀察他們並且傾聽他們,我喜歡他們的作品,如果說我沒受到他們的影響,那是騙人的。最近,我也常用我女兒反對我的意見來衡量我自己。
你最近日常生活中或有什麼重大的事情帶給你啟發嗎?
事件和情境都會啟發我,不過我時常不知道它已經發生,之後我才會在我的作品中發現。我相信它不斷地發生,這樣是很好的。否則我將無法在商業環境中生存。

生活態度影響作品,你通常怎麼渡過日常的 24 小時?週末呢?
我是個自由工作者,我也許同時有許多工作,或者一個也沒有。也許是星期一或星期天,我常會在我工作室附近散步,以對於我所沮喪的事情想到一個視覺上的解決之道。或者,我也可能工作到早上四點(我喜歡在晚上工作),有時我也會追蹤那些我正在等待的客戶電話,我也許會在城裡亂晃,去安排工作、採買,和一些人見面,或去談一些可能賺錢的工作,或者在電腦上剪輯一些音樂,在長島的大西洋海岸游泳,在加拿大或法國的阿爾卑斯山滑雪。所以我通常在早上十點前起床,然後電話開始響,做早餐,收電子郵件並且整理一番,這讓我更快進入工作狀態,因為工作很少在傍晚五六點前開始有進展⋯⋯。
如果你不是個平面設計師,你覺得會是什麼?
很多吧,我喜歡旅行,我好奇心很重,我喜歡歷史⋯⋯我喜歡音樂而且它是很抽象的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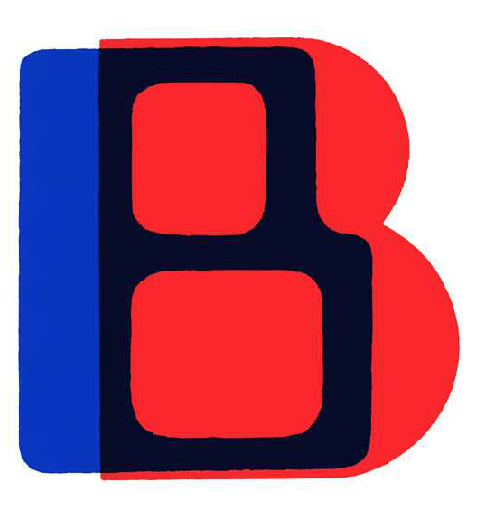

你認為當代設計是什麼?它將何去何從?
我對當代設計觀點有點模糊,我對電腦有著很複雜的情緒,對於擁有電腦效果後,不知道自己這樣的職業是否有新的定義,卻又對電腦這個工具有宗教般的崇拜。
電腦使現在有成千上萬的人都自稱自己為「平面設計師」,一方面可能是好的,電腦讓人有自信、能力,而且也為這樣的藝術表現工作打開了一扇門,另一方面卻也讓這個職業變得平庸,好像每個路人都可以做。
而且現在傾向由藝術層面轉為技術層面,平面設計師變成了平面技師,我幾乎沒看過全靠電腦創作出來的作品,能讓我驚訝或是讓我有所啟發。人都需要一些參考以激發創作的靈感,但現在卻都變成電腦程式,而且現在每個人用的軟體硬體都相同,這代表每個人的思考方法也都延續相同的模式,也許因為地區間的界線逐漸模糊。所以瑞典跟南非,或是波蘭跟阿根廷的作品,看起來差不多,表現方式也大同小異,真正受害的是原創性 ,獨立思考,和真正的創意。但其實我也沒那麼在乎,畢竟一個人的創作要專心在他/她個人的藝術性、設計感、視覺真實、才能去發展更個人更深層的作品,希望有一天可以被這樣的藝術家們圍繞,這樣我就能夠將自己的影像拓展到相同的地步。對電腦我有最後一句話說,顯然現在我們並無法忽略這個工具,但應該要有方式讓年輕人試著用頭腦和想像力去思考畫面,而不是運用電腦,或是使用已經出版的視覺解析刊物,通常還有著令人存疑的美學品質,我認為概念應該要試著無中生有,然後再從五花八門的技巧中,產生新點子。

以你來看,過去五年最好的發明是什麼?為什麼?
誠如你所見,我不在乎那些發明。每天都有東西被發明,但除了醫學或是解決飢荒的方式,每件新發明都加速並節省時間去填塞某部份,似乎總是很自然地塞到最大值。到了最後我們的生活品質有比較好嗎?我們的工作,我們生活中的愉悅有因此而被改善嗎?
有了更多的時間,我們有更輕鬆或更有創意嗎?更別說一連串與製造目的不相關的環境污染和垃圾,速度的變化令人著迷但也 可能失控,我真希望發明一個系統能夠激發人們對地球的重視,而不是只想著怎麼賺錢然後把地球他X的搞壞。
可以給想要成為平面藝術家的人一些建議嗎?
給未來的平面藝術家一些建議:做你自己,樂在其中,學習不同的文化和傳統。假如在中國,請學習你們美麗的文字,學習使用毛筆和墨水來做字體圖像,反抗美國垃圾,好好想想。

你的下一步?
我的下一步,我不知道。我想要更令人驚喜,我希望那對我來說,很巨大、有趣和充滿新意。
當你過世後,你希望如何被人們記住?
我希望人們記住我是一個有做過好作品的人,這些作品歷久彌新,而且對於偉大這件事有些貢獻。■



-1-1536x806.jpg)
-1536x806.jpg)



-1536x806.jpg)

